初见那“婊子”,是在晋城门那的一个歌厅里。那时候,我的一个朋友给那个歌厅送酒水。我给朋友帮忙,说是去帮忙,其实也是开工资的。只是临时而已。
那婊子是那歌厅里面的公主,是那个歌厅公主里最漂亮的一个。因为她的漂亮,我常常情不自禁的看她。也偶尔会找个理由去搭讪。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年纪,还是涉世未深的那种见识,以为她只是一个里面的服务员而已。由于那个歌厅是我供酒水的范围,常常会去那歌厅坐着等老板的发话。所以和她也会聊聊天,聊着聊着,突然吧台座机响了。一个她的同事接到,朝着她喊:“X丽,接电话”。(她们的名字全叫“XX丽”,姓张的叫张丽,姓王的叫王丽,姓李的叫李丽。)她听见叫她后,做出特别厌烦的表情,好像已经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了。给我说让我去帮他接一下电话,就说是她现在很忙,没空接电话。我接起电话,那边是一个粗狂的老男人声音,直接就说:“我亲一口。”我听的木住了,那男人继续说下流话:“我想你的奶子,想你的屁股。”我还在心里低估;“她怎么会找这么个男朋友?”听那男人已经说了好多下流话了,我才加了一句:“她现在很忙没空接你电话。”话音未落,就听那边男人:“你妈了隔壁。”的骂行活了。我压了电话。后来这种电话我陆续接过三次,三次是不同天数,也不是同一个人的。
和那婊子单独接触最近的一次,是她让我去给她帮个忙。说是她出租屋的锁子坏了,让我去给她帮忙换一个。我想,换个锁子是个很简单的事。也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,能和她单独相处一下。
跟着她三拐两拐,在军分区后院的房顶阁楼上。有一间独立的房子,房子就一扇门,门是木质的那种老式木门。她到门口,门一推就开了。进门之后,我一看那门,就不是换锁子的事。显然那门是被人从外面用脚踏了的,门框上安装锁窝的地方,一大块没有了。露出一块新木头茬,一片子木头成不规则半月型形状在地上掉着。那锁子虽然松了,但还完好无损。只是那半月型木头上连着锁窝。
我给她说,这锁子没办法给你换了,得找木匠。她说,那没办法换就算了,完了她找个木匠。
活干不成了,于是我们就开始在她那里聊天。房子,是一个较大的单人间。南面靠墙摆放着一张单人床,房间摆着那种时期的转角沙发,一组一组挨着的那种。最显眼的是她在窗子上如彩旗一样,挨着挂着的三层各样内裤和的胸罩。就连床头也有搭着一两个内裤及胸罩,好像一切是胸罩和内裤的天下。
沙发前面的茶几上,胡乱散扔着那个时代女孩子吃的包装零食,什么薯条,虾片之类。
我们寒暄一阵,她过去散漫的躺在单人床上。像一只美人鱼一样,斜躺着靠在后面叠着的被子上。头发斜披下来,盖住了额头。那时候她的头发非常飘逸,也散发着那种年轻女孩该有的青春气息。
我郑重其事的坐在她的沙发上,看着她聊天。那时候的她还挺纯,脸上带着稚气。显示着青春和活力的诱惑,聊起天来很诚恳,眼里泛着真诚、善良、和妩媚。
寒暄中得知她比我大两三岁,家是金塔某乡的。现在说不上是哪个乡,当时也记不住,或者就没准备记住她哪个乡。我问了她在那里上班的收入,她说了。按照那个时候,我朋友给我的工资。应该她在那里的收入,是我的三四倍。我说那也可以,她说:“哎。好撒?家里人问,都不敢说是干这个,就说是在酒店端盘子呢!”
那时候,我天真的都有点愚蠢。我还安慰她说;“这有撒不能说的,你的活又清闲,工资又高,还光上个晚上的班。”
那是我和她聊的最多,单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。那是个夏天,一个天很热的下午。聊着聊着,她似乎有点瞌睡了,睡意朦胧的半眯着眼睛,做出懒洋洋的姿态。有半句没半句的说话。我便告辞了她,走了。
过了两天,我那个朋友问我。说我是不是在和那个女子拍拖,我说没有的,只是和她聊一聊天。然后我朋友就欺负我,说我和她咋了咋了的。我就想,哪有那么容易的事。那朋友才给我说了,那个女子是干什么的。从那才知道,那里面的公主是干什么的了。当然也会领悟,那是多么容易的事情了。
不过,知道了她是干什么个工种以后,就再也没有理过她。连句话也没心和她说了。一来是她让我很失望,那么好,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。让人天上到地下的落差失落。二来是她岁数比我大。她和我变成了比陌生人,还陌生的关系。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的陌生。
后来见,就是一两年以后的事情了。偶尔看见她进入了一个离我们家不太远的邻居院子,然后的后来经常看见她进出那个院子。原来,她租住在那家的出租屋了。
好像住了不到半年,那个房东男人也是个爱说粗下流话的老男人。开玩笑时没高老低的。我就说了一句,说那个女子咋不见了。她就开始拉起话茬,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演说。说那个女子了不得,把他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招过来了。不论是收破烂的河南人,还是修鞋的瘸子。更甚者,半夜三更的来人敲门。还有大白天的,在他门口杏树底下还蹲两个排队的。他实在没治了,想以涨房租的办法把她撵了。别人是一间六十给她八十,八十她也答应了,后来又涨一百,一百也答应了。到了最后,他直接说开了,让她了搬出去。
其实,那个房东说话夸张呢也不夸张。我的确亲眼看见有两个男人在他杏树下抽烟,但不确定是给他排队的。
那个女子也可能是和她亲近的人多了,我和她的那种按我来说不亲不淡的接触,她可能早已忘却。感觉上是,我认得她,她不认得我。我们相见对眼的时候,她一点认识的感觉也没有。我也报着看陌生人一样的,淡淡的瞄一眼而过。只是我的心里知道我认识你,你是撒人。
又三四年以后,和朋友聊起那个歌厅,说起她。朋友说那个女子现在乱的很,或跟着倒爷到处跑,或跟着在山里开矿的去矿山里。还下流的说被开矿的带到矿山上,给他的工人们搞福利。听上去就让人恶心的极点的感觉。
但是过了一段时间,我在河西山庄后面的那个鱼池上钓鱼的时候。我又看见了她,她围着一个看上去很有钱的男人。那男人虽然夹个公事包,但看上去也露着俗。不像是很高贵的那种富。
那婊子依然很潮气,秀发披下来,皮肤依然白白嫩嫩的,脸上依然很是清秀,从我身边过去,依然散发着化妆品的清香。白色的纱衣,胸罩的吊带忽隐忽现的透着媚,下面是黑色的,那种时尚的齐逼小短裙。那纱衣,比新买的还新鲜,白色的飘渺着,袖口的薄纱随着她的身姿如一只洁白的蝴蝶,在一双高跟鞋的衬托上,围绕着那个有钱男人飞舞着,飘逸着。时不时的用即温柔的又甜蜜嗲哩嗲气的声音,似乎惊恐着,喊叫着,乍着婷婷的邈气的胸,翘着圆圆的性感的屁股,“又一条。又一条。”说着,嗲着,尖叫着,惦着脚尖原地踏步式的跳着,就像一只可爱的小兔。乖巧着,嬉闹着,天真着,显得可爱至极,暧昧至极,骚水泛滥至极。
此时的我已经不是那个纯的愚昧时段,依然是一个经历过世纪的油条。看到这里,似乎是荷尔蒙激素的强烈刺激。似乎忘了我对她的成见和排斥。也许这是每一个男人的通病,被表象所冲昏了头脑。在那里,一边钓鱼一边盯着她看。鱼上钩了没有,根本无法领会。此时只有一个心情,就是羡慕嫉妒那个男人。幻想,如果我此刻如果是那个男人,此时还钓什么鱼?要么扔下鱼竿,去那个旁边的小房子。最起码,会把她拉如后面的那个树林里。
不过,后来回到家了,躺在床上。当那情绪过去以后,还是看不起自己了。明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,那恶心的过往又回想在眼前。
再后面的一次,我在一个牛肉面馆碰见。她和一个也是老男人吃饭,我无意中看见她。她还是那么出众,还是我在鱼池那看到的一个样子。我看她的时候,她也看见我。她似乎也是在想:“这个男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?”我们相对盯了几秒,那男人问她:“你认识?”我赶忙转过身来,就听见她给那个男人说:“烦死了,男人一见我都看,和你一样,都是些色男人!”听见这些话,我几乎恶心的坐不住。很想上去说一句:“你不过就是只野鸡而已,我看你是我奇怪你这只野鸡还活着?”话都到嘴边,又忍住了。看见她,就能看见她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什么货色了。屎跟前围着的,那肯定是苍蝇。
我饭都没心吃了。
从那以后就不见多少年了,似乎已忘记了她的存在。在记忆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就在前天,我坐在店门口聊天。突然从东边的远处,一个高挑的,带着气质的女人,从那边走过来。我一眼就认出是她。她看上去比先前成熟了许多,也高了许多。身材越比那时候直正了,腰还是那么细,头发依旧披着,穿一身蓝色套裙,长的过了膝盖,到了小腿那里,裙摆像窗帘一样的横向打着折。走路依然是风摆柳似得,这腿换在那腿上。高跟鞋依旧咯噔咯噔的。走路时腿夹的紧紧地,可能是没有生过孩子。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,我仔细看她,虽然远看直正挺拔。那披下来的头发已经没有了她那时候的光彩和飘逸。虽然湿但不滑,虽然黑却不软。脸盘子也比原来大了,腮帮子后面的骨头也鼓了出来,但脸上没有邹褶,面目没那时光鲜,但还亮丽。那胸也不是原来的那么圆润,而是像奶牛的大吊奶,用一块布尽力兜着,晃荡来晃荡去。屁股也还挺翘,走路提着,左右交替晃荡着,就是胯子宽了许多。比起在那时候歌厅里见的时候,那时候的她和现在的她,现在的她就是那时的她妈。
这婊子老了,老了许多。幸会的是她有一个好底子,天生一个漂亮胚子。她也可能曾为此而骄傲,也为此而自豪过。可惜了,不知道是社会毁了她的一生,还是她家里的条件,让她把青春廉价的出卖了。她把她的天真和浪漫,廉价卖了。也说不上这世界,这社会上是男人太坏,创造了她的意识形态,还是她就自甘堕落决定了她的一生。
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如此的自信和坚强。她依然活着,依然又闯入我的视线中。而且看不出她原来的生活和现在的处境,没有让我看不起她那堕落的样子。猜不透她是如何活着的。
即恶心,又谜一样的女人。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单身,是否还在随便跟着人乱跑,也或许嫁个好男人,过着一般的生活,也或许会做个小三,再转成正房。我祈求上天保佑,她至少不会是和以前一样,租个单人房子重操旧业吧!请不要让她太惨了,这个唯独我不是她的顾客的,把全天下男人都变成连襟的女人。
听说,她在那个歌厅上班的两个同事。都已经从小三转正了,一个挤走了河北人的正房的卖鱼小老板,姑娘都已经十几岁了。另一个跟着上了山东,开着个超市,日子过的也很好。
只有她,是一个骨子里本性老实善良的人,一个不坏的婊子。也可能不忍心拆散别人家庭的善良婊子。吃亏一辈子的婊子。
看着她,从东面过来,经过我的面前,又从我面前,一直消失在西面,融入在太阳的余晖里,太阳的余晖从她身体的轮廓里透过来,隐约了她的身影。像一团谜一样的消失了。
正如她的从东面一路走过我身边,一路向西依然坚挺,一路平淡,一路艰辛,也即将落入流年的落日余晖中。平平淡淡默默无闻。有过天真,有过风情万种,有过惨淡艰难,有过没落与坚强。
正如我眼中的许晴,有过提着鞋彰显着青春气息,撒娇着让男友背着她过马路上楼的情节。也有人老珠黄后在《老炮》里让冯小刚蹂躏着的奶牛般的下垂大奶,和半露的大屁股。
她们依然是她们,让人动心,让人失望,让人感觉平庸的,带有失落感的低迷射线。
正如我一样,从当初远大的报复,和现在平庸的生活直到现在。
依旧平淡,还不如初。
和那个婊子一样,老了。困了。乏了。看淡了。想通了。
当初恶心别人。
现在恶心自己。
我又比婊子好到哪儿了?
依然无所作为,依然碌碌无为,依然平淡如故,夕阳的余晖就在那里,随时准备着要吞没你的身影。
殊途同归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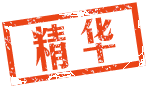
 微信小程序
微信小程序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 微信服务号
微信服务号 微信客服
微信客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