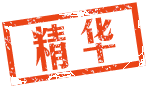小说《遗精》(上部)
今天是粮食局牛局长的儿子、县委组织部牛行干事与袁县长的千金、师范学校袁枚老师结婚的大喜日子。婚礼上新郎那平静的神态,加之新郎、新娘间外貌对比上的悬殊,带给人们很多猜想。牛行也真是的,给人感觉象是包办婚姻,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喜悦的神色,偶尔笑笑,也笑得非常勉强。新娘一直在留意他,看他那样,那欢笑也似乎是藏着掖着的,未能尽情尽兴,多少有些尴尬。都什么年代了,哪里有包办婚姻呢,所以有些敏感的人又说可能有政治上的因素。可了解两家家庭情况的人,又不同意这种说法。县长是个作风硬气、正派的好官,局长呢,也老实厚道,并不是一个喜欢钻营的人,除了人品上有“是猩猩惜猩猩”的相似,别的一定不会搭界。人们要猜忌,要嘀咕,谁还能管得住谁的那张嘴不成,又不是演算数学,也不是侦破推理,非要有个正确答案和客观结论才行,也就不消说得。整个婚礼上,好象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些方面,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在意这场婚礼是什么规格、程序、仪式什么的。结婚仪式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结束了。
按风俗晚间是要闹洞房的。到了这个时候来了十数个年轻人,他们进来后先到处转了一圈。新房自然是比城里一般人家的稍微大一些,也阔气一些,但并不招人眼。悉心的人却是留意了新房墙壁上的结婚照片,出奇得大,几张图画张贴的都是比较前卫的那种,新床上铺陈比较艳丽,卧室的灯光略带红色且有些暗淡,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。男人大抵不会有这种奇思妙想,这样的装饰,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女人的杰作。
闹洞房才闹过三五个节目时就有人察觉,牛行不但没有什么情绪,而且佯装醉酒。一个巴掌拍不响,大家也都兴味索然,很快散了。
前来捧场的热心人走了以后,牛行并没有结束演戏,依然“醉”倒在沙发上。新娘见他这样,给他泡了一杯浓茶劝他喝,还坐旁边陪伴着。新郎闭目养神,一语不发。时间已经不早了,新娘耐不住,就柔声细语地劝他早点上床休息。新郎半睁着眼睛看看新娘,说:“你先去睡吧,我再躺一会儿。”袁枚无奈地走到卫生间洗漱完,回到卧室,先睡下了。她欣赏着由她一手经营的这个洞房,心里感觉很舒服;新婚之夜,心都有些跳,淡红色的灯光掩饰了他面颊的绯红。
新郎在新婚之夜这个样子,新娘并无埋怨的意思,更不会生他的气。可以说,从他俩认识以来,他一直就是这样,那个中感受,真是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
袁枚长得不太好看,脸盘有些大,五官该大的不够大,该小的不很小,要将女人的相貌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的话,她是介于下等偏上、中等偏下的那种。但她又绝非没有长处。她的身材,那可是够婀娜够飘逸的,气质也入流。
袁枚从懂事以来,就心志颇高,从不接触男孩子。他爱看影视剧,特喜欢曾饰演楚留香、乾隆皇帝的那个叫郑少秋的演员,只要是他演的影视剧,她几乎看了个遍,而且最留意的并非剧情,而是演员的个人气质,包括他的容貌,他的演技,所以呢就在心里有了交友的偶象和择偶的模式。
随着岁数见长,父母见她下班后除了看影视,就是看书、睡觉,没有谈对象的动静,心里有些着急,还委婉地劝过她。每听到这样的话,她一般都是头都不回,就一句:“还没遇上合适的;也还小呢”。其实她有很多话并未对父母说,这就是找不到心中所爱,宁可独身过活。她才不在乎男人呢,一般的男人,她简直就没有一点感觉,甚至不屑一顾。就这样过着单身快乐的日子,以至拖到25岁大龄。
这年初秋一个星期日的下午,袁枚在家里闷了半天,想出去走走,就到百货大楼随意地转悠,当走到男女服装区交界的地方时忽然眼前一亮,见一个男人正在男装区看衣服,那个头、相貌、气质、动作、表情都有些像郑少秋,就觉得格外亲切,心里也有了一种异样的冲动,一时竟乱了方寸,站在那儿一动不动,服务员的一声询问,才使她回过神来。见他在那儿试衣服,和服务员交谈,她走又不舍,不走站着也不象,就学着他的样子,在那里逗留着,眼睛却一刻也没离开过他。一会儿,见他走了,她心里又是一阵惆怅,思忖他这一走,怕是再也不会有机会结识他了,那可真是可惜。心里这样想着,就不由自主地跟他下了楼,走出了商场。她想不方便过去和他搭话,但跟着他,寻出一点踪迹也好。机会是自己把握的,不能不付出努力就失去二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机遇。她不远不近地尾随他,走过大街,插进一条巷道,走不远,见他进了全城人都知道的一个住宅小区。好在一直没见他回头,她就跟进去,眼看他进了一单元……
袁枚这样痴痴地想着,一看墙上的挂钟,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,洞房花烛却独守空房,心里没着没落,就又起来来到客厅。见他依然躺在沙发上,好象睡着的样子。袁枚准备推醒他,手刚伸到他身上,又犹豫了。他这两天也着实忙坏了,怕是真累了,不如让他再睡一会吧。她走到卧室,拿出一床毛巾被,轻轻地盖在他身上,就又回到卧室里钻进了被窝。所谓孤枕难眠,她心里也不是滋味,恨不能马上把他拉到床上来,表达无限的柔情蜜意,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。可看他那样也不好强求,总不能在新生活的第一天就惹他不高兴吧,也就只好忍着。
她能得到他,实在是不容易。
她认下了他所居住的住宅小区,悻悻然地回到家里,整个人就象是丢了魂魄似的,不知做什么好,也好象已经不记得以前都做了些什么,在书桌前闷坐一阵,打开电脑胡乱点一阵,又在床上躺一阵,眼睛望着房顶,眼前却闪现着他的身影。她盘算好了,到了下个周日,她一早就去小区门口,守株待兔。可是,就算他出来了,又该如何呢?一个女儿家,直接冲到一个男人跟前,不论说什么话,总是一件很莽撞的事。你说随便问件事,比如找人、问路什么的,进入不了正题;直接说“我喜欢你,想认识你”?男人做出来虽然有失体面,但也还算不上是丑闻,可女人这样,实在是有些轻贱。要不,等到他再说吧。正这样用心构想着,听到母亲叫吃饭了,才把她拉回到现实中来。
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周。这个星期日她早早起床梳洗,着实打扮了一番,换上了自以为最为得体的衣服,十点钟就出门来到了小区门口。这是一个中国西部的中等城市,这时候从马路上来往的人也不是太多,尽管如此,姑娘家老是在那里站着也怪怪的。来回走了一阵,又在门口站了一阵,到午间了,她见马路对过一家门市部门口摆下了茶摊,就走过去,要了一杯杏皮水喝起来。摆摊的是一个老太太,因为她是第一位顾客,算是给她开了张,所以脸上挂着笑,对她说这问那的。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老太太说着,眼睛不时地扫视小区大门,生怕他出来走了,自己还没看见。一杯杏皮水在不知不觉中喝完了,干坐着又不好,于是她又要了一杯。又坐了一阵,抬腕看表,已经快一点了。她寻思,一般星期日外出办事的人,比平时多睡一阵,起来收拾一下,出门也到十点左右了,逛街的人一般吃过午饭,一点前也都出门了,现在不见动静,八成是等不到了吧。这样一想,就付了账,起身回家了。半天的心思精力就这样白费了,她心里的感受何止是失望,简直就是酸楚。她检讨自己,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在星期日上街闲逛或有事可做,但其它时间总是要上班的,肯定能等得到。想到这儿,就拿起手机,给校长打电话,说是病了,请了星期一上午的假。星期一这天,她又起个大早,收拾完就出了门,到小区门口时,离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。等了有十几分钟,果然见他出来了。虽然没有走过去的勇气,但能跟着他,再探到他的上班地点,就又多了一份希望。他跟随他一直到了县委门口,见他上了机关大楼,心里高兴了,一看上班还来得及,就赶回学校去。
袁枚记不得有什么事儿靠过父母,让父母帮忙办过什么事,但这事,她想来想去,不求爸怕是不成,而且还不能够绕弯儿说。午饭时她就引出了话题。
“爸、妈,你们不是老催我找对象嘛。”
母亲一听抢了嘴:“是该找了孩子,你的事不能再拖。”
父亲看了老伴儿一眼,就看着女儿,听她怎么说。
袁枚见爸的神情是在等她的下文,便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看有个小伙子不错,他和爸在一个楼上办公,可就是……不知道他叫什么,做什么工作。”
也不用父母盘问,袁枚又接着说了这个人的外貌特征,最后补充一句:“我是在县委门口遇见他,看见他上了县委办公楼。就这么多。”
父亲一听,随口就说:“他叫牛行,是组织部的副科级干事。”他说完,就没再说什么。心想女儿也算是有眼力了,一直不谈对象,原来心这么高。这个小伙子长得的确一表人才,人品好,能力强,是单位的骨干,很有发展前途。他想把这些情况一并介绍给女儿听,但转念一想,听说机关上大部分人都给他介绍过对象,都没谈成,耽误了几年,比女儿大两三岁了,还是单身,那他的心眼就很高了。目前还只是女儿的一厢情愿,说得太多,事情不成,对女儿伤害太大。
“老袁,你怎么不说话了?快想个办法让女儿认识一下。女儿的事真的不能再耽搁了!”母亲按捺不住,这样一催,打破了一时的沉默。女儿接口说:“爸,你要没意见,就找个人帮我介绍一下吧。”
其实父亲对他这个宝贝女儿的事也不是不急,只是不象老伴儿常挂在嘴上唠叨,就答应了,让女儿等他的消息。
袁县长回到单位后,觉得让谁给帮着提这门亲都不合适,秘书吧,好象是传领导口谕,他的搭档或是部属,也还都是圈内人,要做到他不知情的样子还真难。绕来绕去,他给一位曾经共过事,对两家都熟悉,现已退休的一位老朋友打了电话,拖他做媒。这位朋友第二天就到牛局长家提亲,当着一家的面摊开说了此事。牛局长见过袁枚,虽然在人材上有些配不上自己家的孩子,但那女孩看来倒是端庄贤淑,也大气,让晚辈们接触一下也不是坏事,于是表态说没意见,主要是看孩子的意思。局长的老伴儿一直封闭在家里,不知道外面的事,也没说什么。他又和牛行谈了。牛行虽然和袁县长一起工作,可从未到过他家,也从未见过他女儿,所以答应见见面再说。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天晚上,媒人带着袁枚来到了男方家里。大家一起说了一阵子话,大人们就都躲到另屋里闲聊了。年轻人这边,袁枚就象和对方是老相识一样,毫无拘束,落落大方。牛行也健谈,只是表现非常平静,情绪上不象袁枚那样有起伏。他们各自谈了一些工作方面的情况,互相留了电话。
媒人是和袁枚一起出来的。问起袁枚的意思时,袁枚并未掩饰自己的想法,求媒人设法促成他们的这桩姻缘。 |